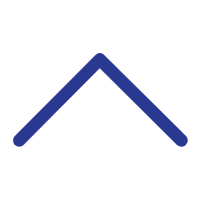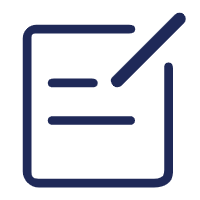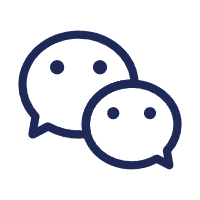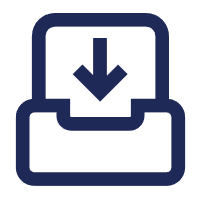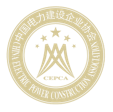地下1820米!我國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發(fā)現(xiàn)全球最深砂巖型工業(yè)鈾礦化
7月18日,中核集團(tuán)專家團(tuán)隊宣布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地下1820米發(fā)現(xiàn)全球最深的砂巖型工業(yè)鈾礦化,刷新了世界砂巖型工業(yè)鈾礦化發(fā)現(xiàn)最深紀(jì)錄,標(biāo)志著我國在深地砂巖型鈾資源勘查方面處于世界領(lǐng)先水平,為全球鈾礦資源的勘查與開發(fā)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撐和找礦思路。
鈾礦勘查的目的是探尋和確定具有工業(yè)價值的鈾礦床,并評估其資源量和開發(fā)利用前景,工業(yè)鈾礦化是尋找工業(yè)鈾礦床的直接可靠線索。本次發(fā)現(xiàn)的工業(yè)鈾礦化是我國首次在塔里木盆地沙漠腹地空白區(qū)紅雜色層中發(fā)現(xiàn)的厚大工業(yè)鈾礦化,填補(bǔ)了我國最大沙漠覆蓋區(qū)的找礦空白,意味著我國鈾礦勘查突破了砂巖型鈾礦成礦理論禁區(qū),在“天-空-地-深”三維探測技術(shù)基礎(chǔ)上,集成建立了一套適合荒漠-沙漠覆蓋區(qū)的砂巖型鈾礦綠色高效探測技術(shù)體系,實(shí)現(xiàn)了新區(qū)、新層位、新類型、新深度找礦突破,對我國砂巖型鈾礦找礦具有示范引領(lǐng)作用,將大幅提升我國在荒漠-沙漠覆蓋區(qū)鈾資源勘查能力和水平,為我國核能事業(yè)的穩(wěn)健發(fā)展筑牢根基。
為推動塔里木盆地鈾礦找礦突破,夯實(shí)鈾資源大基地建設(shè),在國家原子能機(jī)構(gòu)的指導(dǎo)和支持下,中核集團(tuán)的核工業(yè)北京地質(zhì)研究院聯(lián)合核工業(yè)二一六大隊成立了一支塔里木盆地核能開發(fā)科研專家團(tuán)隊,創(chuàng)新提出“滲出-滲入復(fù)成因區(qū)域預(yù)測模型”,創(chuàng)新發(fā)展砂巖型鈾成礦理論,開發(fā)塔里木盆地復(fù)雜地層深孔高效鉆進(jìn)技術(shù),為本次砂巖型工業(yè)鈾礦化找礦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撐。
深度閱讀
沙海尋鈾
用雙腳丈量56萬平方公里找礦禁區(qū)
用青春鉆透1820米地層
塔里木盆地中部,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2024年初冬。
當(dāng)鉆頭艱難穿透地下1820米的巖層,放射性測井儀顯示屏上突然躍動的曲線,如同生命的脈搏,宣告全球最深砂巖型工業(yè)鈾礦化的發(fā)現(xiàn)。零下20攝氏度的嚴(yán)寒中,核工業(yè)北京地質(zhì)研究院鈾資源探測研究部總工程師郭強(qiáng)和團(tuán)隊成員劉念跌跌撞撞跑向沙丘高處,顫抖著用手撥通了衛(wèi)星電話:“找到了!厚度8米多的工業(yè)鈾礦化!”
這個曾被國際地學(xué)界判定為“找鈾禁區(qū)”的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終于被中國核地質(zhì)人撬開堅硬外殼。
“禁區(qū)”突圍
這么多年來,塔里木盆地找鈾始終是懸在中國鈾礦人心頭的未解之謎。中核集團(tuán)首席科學(xué)家、塔里木盆地項目負(fù)責(zé)人秦明寬攤開地質(zhì)圖,手指劃過56萬平方公里的黃色區(qū)域。與這片區(qū)域相鄰的中亞地區(qū)坐擁百萬噸級鈾礦藏,而一山之隔的塔里木盆地,歷經(jīng)多年勘探卻收獲甚微。
這片位于我國西北的巨型盆地,是我國第一大沉積盆地,面積比鄂爾多斯和松遼兩大產(chǎn)鈾盆地之和還要多出近5萬平方千米。然而,這片廣袤的土地卻成為了鈾礦找礦的“硬骨頭”。
盆地周緣構(gòu)造復(fù)雜,中新生代以來經(jīng)歷了多期強(qiáng)烈的構(gòu)造運(yùn)動,盆內(nèi)荒漠沙漠廣布,沙漠覆蓋面積高達(dá)33.7萬平方公里,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鈾成礦條件極其復(fù)雜,找礦面臨巨大挑戰(zhàn)。2018年,關(guān)于塔里木盆地找鈾的戰(zhàn)略研討會上,質(zhì)疑聲不絕于耳:“沙海找鈾無異于大海撈針。”
轉(zhuǎn)機(jī)源自一次顛覆性認(rèn)知。秦明寬帶領(lǐng)團(tuán)隊梳理30年勘探數(shù)據(jù)時注意到,遠(yuǎn)離盆地邊緣的紅層中存在放射性異常,他敏銳地意識到該盆地主盆區(qū)廣泛分布的紅層在特定條件下完全可以成礦。基于塔里木盆地的地質(zhì)和地形地貌特點(diǎn),創(chuàng)新研究思路,他鮮明地主張打破以往“暗色沉積建造”和 “盆緣找礦”的傳統(tǒng)找礦思路束縛,將找礦方向轉(zhuǎn)向了長久以來被視為找礦禁區(qū)的主盆區(qū)“紅雜色”新層位和“盆地沙漠腹地”。“既然與塔里木鄰近的中亞地區(qū)能大規(guī)模成礦,廣闊的塔里木盆地深部為何不能形成鈾礦體?”2020年,他力排眾議申報國家原子能機(jī)構(gòu)重大科技攻關(guān)專項,組建起一支30余人的攻堅團(tuán)隊,其中半數(shù)為擁有博士學(xué)位的“80后”、“90后”。
“我們要進(jìn)軍盆地腹地,挑戰(zhàn)找礦禁區(qū)!”項目啟動會上,秦明寬的宣言擲地有聲。短短四年時間,團(tuán)隊多次實(shí)地考察,創(chuàng)新性提出了“滲出-滲入復(fù)成因預(yù)測模型”,明確了盆地找礦新層位和新地區(qū),創(chuàng)新發(fā)展了砂巖型鈾成礦理論;將遙感、地球物理、地球化學(xué)等多技術(shù)方法熔鑄為“透視之眼”,洞穿沙漠厚覆蓋層,探尋深部鈾礦蹤跡。團(tuán)隊成員肖菁通過與中亞大量地質(zhì)數(shù)據(jù)對比研究,為研究課題提供了關(guān)鍵佐證:“塔里木與中亞鈾礦富集區(qū)存在相似成礦地質(zhì)特征,具有巨大找礦潛力。”
從理論上,這里極有可能成礦!
“沙海”長征
塔里木盆地廣袤的沙漠腹地,狂風(fēng)卷起的沙塵模糊了天地界限,晝夜溫差高達(dá)30℃。“這里,沒有飛鳥,沒有綠草,只有無盡的風(fēng)沙和熾熱的陽光。是的,這里是一片‘無人區(qū)’。我們要在這里開始和時間賽跑了”。得到理論驗(yàn)證后,真正的尋鈾之旅開始了。雖然做鈾礦地質(zhì)科研已有10余年經(jīng)驗(yàn),但這種長達(dá)數(shù)月深入“無人區(qū)”還是第一次嘗試,郭強(qiáng)在自己的本子上記下了上面的文字。
2021年4月,劉念的首次踏勘就遭遇下馬威。越野車在千里荒漠中顛簸,窗外只有肆虐的風(fēng)沙。“背著數(shù)十公斤設(shè)備和樣品徒步兩小時是常態(tài)。”他告訴記者。
更兇險的考驗(yàn)在次年夏季降臨——當(dāng)肖菁帶領(lǐng)小組深入天山山谷取樣時,烏云瞬間吞噬晴空。“快撤!山洪要來了!”。暴雨傾瀉中,團(tuán)隊護(hù)著樣品奪路狂奔。年輕師弟顫抖的聲音刺破雨幕:“師姐,我還不想死,我還沒結(jié)婚呢!”當(dāng)最后一人撲進(jìn)車廂,洪水已漫過車輪。
“我們基于智能化算法,首次構(gòu)建了一套適用于巨型復(fù)合盆地和荒漠-沙漠覆蓋區(qū)砂巖型鈾礦找礦智能預(yù)測方法,據(jù)此預(yù)測成礦遠(yuǎn)景區(qū)10片,圈定了找礦靶區(qū)。應(yīng)該說,定位的精準(zhǔn)為我們節(jié)省了大量的時間和鉆探量,即便如此,我們的實(shí)地鉆探依然開展得非常不順利。”郭強(qiáng)回憶。
2023年,郭強(qiáng)最大的壓力來自于遠(yuǎn)景區(qū)的鉆探查證優(yōu)化論證。沙漠的脾氣反復(fù)無常——白天,地表溫度超過50℃,夜晚溫度卻急轉(zhuǎn)直下;沙塵暴襲來時,隊員們只能用身體壓住圖紙,防止資料被風(fēng)卷走;飲用水靠每周一次的車隊補(bǔ)給,洗澡成了奢望。
更棘手的是人員和設(shè)備的“水土不服”,柴油機(jī)在高溫和沙塵下頻頻罷工,鉆遇松散砂層時,鉆孔如漏斗般塌陷。“四任鉆機(jī)機(jī)長打了退堂鼓,鉆工換了一批又一批。”找礦邏輯論證再縝密,也需要鉆孔一個一個打下去才能得到驗(yàn)證。郭強(qiáng)在重壓下常常通宵失眠,眼底布滿血絲。
深地回聲
真正的硬仗在2024年打響。
隨著鉆探查證的不斷推進(jìn),深部找礦線索逐漸顯現(xiàn),沙漠深部鉆探查證區(qū)現(xiàn)場負(fù)責(zé)人劉念的神經(jīng)始終高度緊繃,由于沙漠腹地幾乎沒有路也沒有信號,驅(qū)車從沙漠邊的駐地到鉆探現(xiàn)場需要4個小時左右,為了盡可能在現(xiàn)場多獲取一些地質(zhì)信息,他索性住到鉆探現(xiàn)場指揮鉆探部署,白天協(xié)調(diào)各項鉆探施工工作,晚上整理數(shù)據(jù),編制圖件。
隨著時間的流逝,初冬的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被罕見積雪覆蓋,天寒地凍的惡劣自然條件,讓施工方開始“打退堂鼓”,“我們一次又一次的溝通協(xié)調(diào),才能一米一米的艱難打下去。”劉念說。一片雪白中,他堅定地守著機(jī)臺,裹著軍大衣記錄巖心數(shù)據(jù)時,全然不知睫毛上已然結(jié)霜。
鉆探施工方早已經(jīng)忍受不了惡劣自然環(huán)境的折磨,多次提出停鉆要求,現(xiàn)場總負(fù)責(zé)郭強(qiáng)頂住壓力,毅然堅持:“再打30米!我簽字負(fù)責(zé)!”最終測井的那個晚上,郭強(qiáng)和劉念都守在鉆機(jī)旁邊,確認(rèn)了測井儀上陡然上升的曲線后,抓起衛(wèi)星電話沖上沙丘,全然不顧寒風(fēng)灌進(jìn)衣領(lǐng):“我們成功了!厚層鈾礦體!”回駐地后,兩人都因?yàn)槭軆龆l(fā)燒了。
夜幕中,地質(zhì)營地的燈光如星辰灑落沙海。捷報帶來的瞬間興奮背后是一份關(guān)于成長的悠長回味。
曾經(jīng)為了這個項目無數(shù)次論證研討、拍桌子紅臉……但秦明寬覺得這一切都值得:“我們不僅找到礦,更創(chuàng)建了適用于全球沙漠區(qū)的砂巖鈾礦探測技術(shù)體系。”
“好多人問我,你一個博士,為什么要選擇這條艱苦的路?因?yàn)椋覀兊膲粝耄筒卦谶@片沙漠之下,風(fēng)沙再大,也擋不住我們向地球深部探索的腳步。”郭強(qiáng)如是說。
“這個項目不僅是我職業(yè)生涯的起點(diǎn),更是鍛造專業(yè)能力和堅定科研信念的熔爐。每年數(shù)月的野外堅守,意味著對家人陪伴的缺失,心中常懷愧疚。然而,當(dāng)自己傾注心血的研究成果最終支撐起塔里木盆地這一重大找礦突破時,讓我感到更多的是成就與滿足。”劉念如回憶。
肖菁則在備忘錄中寫下:“我始終相信,科研就像在沙漠中尋找綠洲,只有堅持不懈,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感謝塔里木的風(fēng)沙教會了我堅韌,教會了我如何在逆境中尋找機(jī)會,也讓我們這群深愛著核地質(zhì)的青年們看到自身的力量。”(郭強(qiáng) 李娜 鄒耀林 段新瑞)